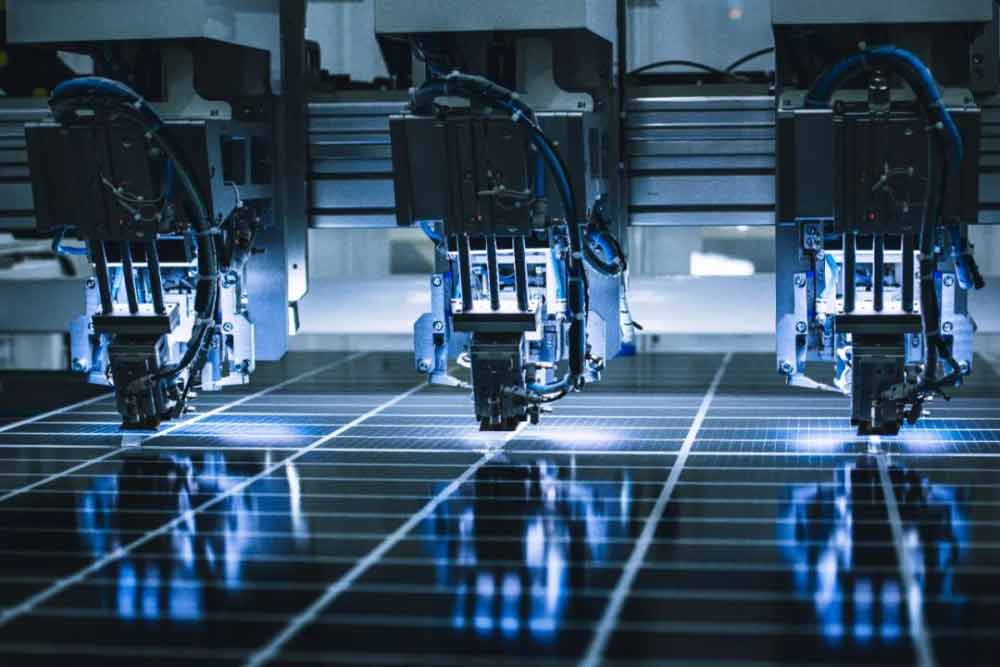一是中西部“风光无限”地区急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,在国家对光伏、风力发电激励政策的作用之下“一哄而上”,导致可再生能源产能过剩,本地无法完全消纳,又无法全部输出,从供给端导致产能过剩;
二是电网企业不愿意接纳输送光伏、风电等可再生能源。可再生能源生产基地多位于中西部地区、需求地区却常常位于千里之外、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,输送距离远、成本高,客观上形成了“肠梗阻”;
三是东部发达地区不愿意使用可再生能源。东部沿海地区一般都有煤电企业,多用当地煤电,不仅可以拉动就业、还可以增加本地的GDP。这样一来,外来的可再生能源即使价格成本相当,这些地区还是更愿意“让肉烂在自家锅里”。至于煤电导致的大气污染等环境成本,只能停留在道义层面了。
笔者认为,第一,国家需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,改善舆论环境,使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。第二,对电网企业加强新能源输配电进行合理补贴。重点放在体制机制建设,以价格杠杆鼓励电网企业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输送、鼓励消费者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。第三,逐步提高对煤炭等化石能源征收的资源税、对煤电等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,通过补贴和税收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“双轮驱动”,一方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、促进我国整体能源结构的绿色化,另一方面倒逼煤电企业改进工艺水平,实现传统行业的绿色化生产。第四,通过社会公益组织环境诉讼和检察院环境诉讼,助力各方共治,防止在能源生产、供给和消费的全产业链当中各方推诿、扯皮,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升。
 切换行业
切换行业

 正在加载...
正在加载...